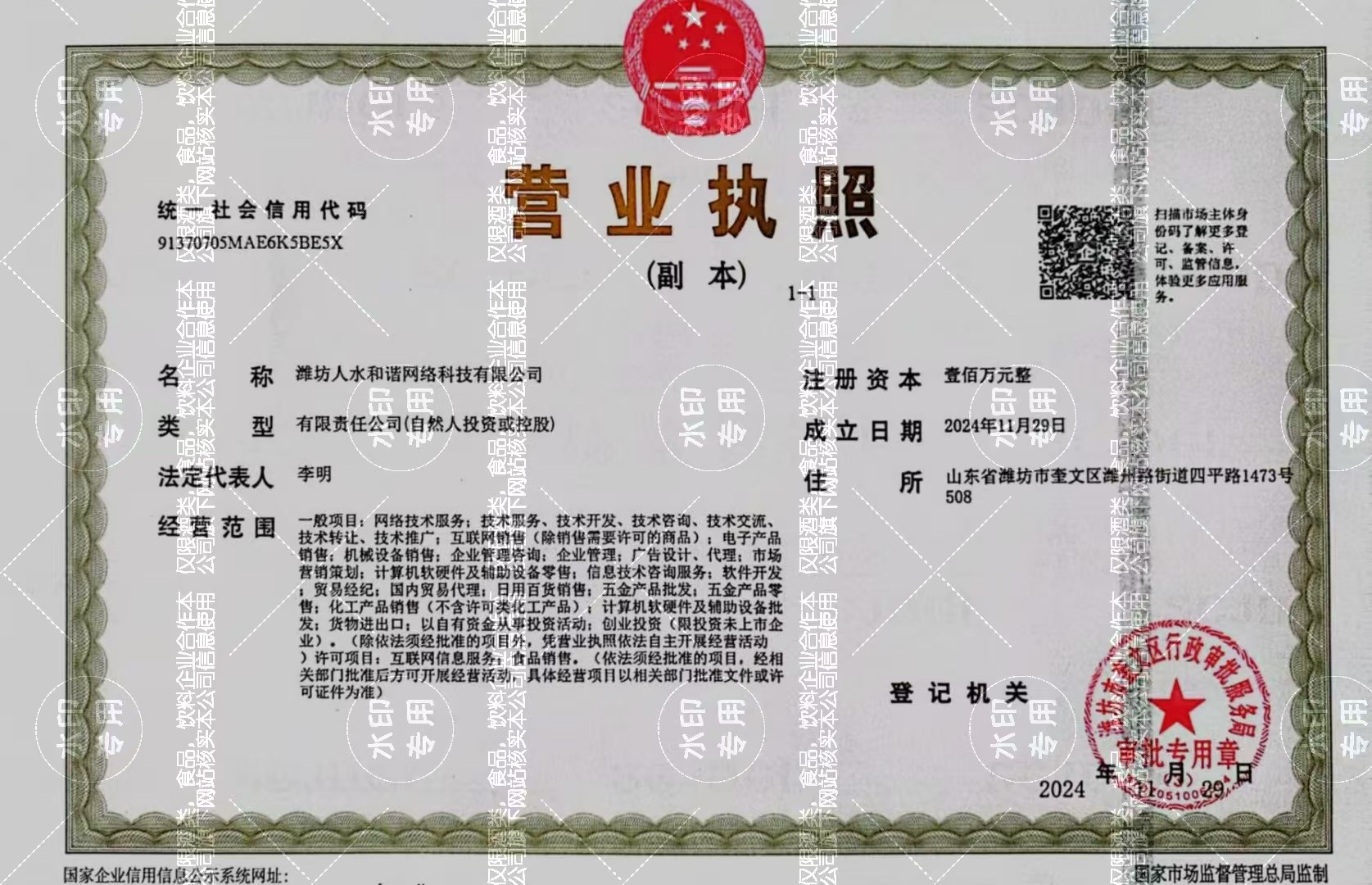“頭刀韭,花香藕”,在鄉俗俚語里之所以相提并論,大約是由于它們的嫩。春韭不必多說,老杜就有一句“夜雨剪春韭”,他在吃韭的時候不自然地冒出了這么一句,似乎吃的不是韭,而是被寒冬壓抑甚久的春意。那么食藕,食花香之藕,則是夏日里一闕清涼的小令。
拐入小巷中的菜市,空氣里彌散著水生草木特有的氣息:野菱的藤子亂麻似的糾纏不清,論堆賣;雞頭梗子淡朱砂色,細軟管般,用水盆盛著;藕并不美,粗細長短不一,雖已清洗過,可外表粗拉拉地泛著黃,只有藕尖那一小截脆嫩白凈,單獨束成一小捆賣,粗壯的藕節則是散賣的。我發現有一根尤其細嫩,可賣藕的女子笑曰是準備自己留下吃的,那甜嫩的滋味可想而知。
水鄉有水八仙,種種皆有煙水氣,藕居其中。夏藕清甜,冬藕粉糯,夏藕生涼意,冬藕添暖氣。藕尖一折即斷,斜切成絲狀,配上紅椒絲,淋以老醋,是伴粥良菜。藕片切得極薄,一順溜兒排在白瓷盤中,潔如白玉,晶瑩剔透,不要滿滿堆上一大盤,撒上白糖,即切即吃,若切多了,半日之后藕片疲軟,就沒有了脆嫩滋味。
夏藕嚼后幾乎無渣,藕斷絲連的情景也極少見,游絲細若無,只有清甜的好滋味,父親吟道:“杏花藕,小酌幾杯淺酒,恰然自樂!”我百思不得其解,這藕與杏花有何關系?季節都對應不上,又怎么取其香氣?但我沒有深究,父親口里保留著很多方言俗語,只要能意會就是美妙的。
讀過周作人的談吃短文,他也寫了《藕的吃法》:當作水果吃時,即使是很嫩的花紅藕,我也不大佩服,還是熟吃好。先生這里將嫩藕寫作“很嫩的花紅藕”,與我父親的叫法似有異曲同工之味。我暗自思忖:這藕上荷花可不就有嬌艷無比的粉紅?這樣想,吃藕,吃花紅藕,也就似有藕花無數了。
藕有不同的燒法,味也迥異。冬日的藕有手臂粗,從抽干水的塘底拖上來,起藕人穿著特制的膠衣,風寒毫無畏懼,那被稀泥糊得不成樣子的藕清洗后顯出粗樸壯實,整筐地挑到集市上去。粗孔的藕塞以糯米,淋以桂花蜜,入屜蒸熟便是桂花藕,街邊推車上的只塞了糯米粒,口感上因此大為遜色,這道桂花藕是深秋季節必做的一道甜點。街邊有賣藕粥的,顧名思食,藕要融入粥,藕塊需燉得入口便化才算到了火候,用長柄的銅勺舀上,撒上白糖一勺趁熱吃,寒風里也就不覺得冷了。
若是在家,如今紅泥小火爐自然是沒有了,但缽子要備上一個,缽子有砂鍋的質地,用缽子燉藕骨湯,藕在肉湯里肥嘟嘟、紅艷艷的,頗有民間的富貴氣。
古人有雅興,以梅為妻,以鶴為子,留下不少佳話。杭州西湖邊小孤山上埋著一縷詩魂,逸著年年梅香。我曾到西湖一游,坐在湖邊吃藕粉沖的糊,簡易的小碗,味清薄得很。當年在西湖邊送友人的楊萬里,見眼前如畫,蓮葉接天,荷花映日,骨子里有著詩情的楊萬里怎會不沉醉呢,看著美,聞著香,吃著甜,于是詩人與芡、藕稱兄道弟起來——“雞頭吾弟藕吾兄”,可謂豪爽至極。雞頭是芡的俗名,江南的景滋養得詩好,江南的詩吟誦得藕甜。
食藕,冬夏皆宜,濃淡都好。








 微信客服
微信客服